西凤 和瑞(西凤天祥和瑞酒)
西凤 和瑞(西凤天祥和瑞酒)
西凤 和瑞凤集团与陕西省商务厅、陕西省工商联合会、陕西省贸促会等单位的战略合作,也是西凤集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。在此次签约仪式上,双方共同宣布将在陕西省内建立“西凤酒文化博物馆”,并将于2018年正式启动建设。
文/王英富
寨子沟二十多里长,沟深山野,村民们移民的移民,外地落脚的落脚,现在留在沟里的全是些孤寡老人,和流岭山捱畔的高山组现在只剩下五个六七十岁孤独老人。
有个年轻时风流妖媚的女人,叫瑞娃,现在也老的佝偻着腰身,乱发蓬蓬,脸上褶褶皱皱能当搓衣板,脸面灰黯无光,整日拄根拐棍,沟上沟下邻居家串来串去,大家依然叫她“瑞娃”。
遇到有人问“你干啥呀瑞娃” ?老婆子瑞娃总是回答“买药呀”。等到太阳偏西,她还在下下一家老人门上,东一句西一句七说八说,重复着昨天、昨天的昨天说过的话:“这天要变了,野猪成精了,把刘平的门开开,住到刘平屋里了。”
刘平是谁?刘平都死了六、七年了,独庄子闲了五、六年,门前场院杂草野蒿长一人高,野猪不去谁去?
已经七十多岁瑞娃的老婆子总是接着唠叨,唠叨着昨天、昨天的昨天说过的话:“你看咱沟里王有财早年害人造下孽了,得个高血压病连跛带睡三年才死,沟底下张星老汉老诚实在积福行善一辈子,坐在墙根晒太阳,太阳没晒完,人就没气了,没受一点罪,看乃多好,功德圆满。唉!小小寨子沟两年走了十二个人,留下三十个人了,照这推算五年就没有了,寨子沟没有人了,也就没有寨子沟了。”
看到邻居儿女来来往往,总是重复着以前说了无数遍的话:“唉!儿女近了还是好,眨眼就来了,吃的喝的用的呜一声就给你拿到跟前了,我儿子在湖北女子在河南,几年不得见,有和没有一样样……”
老婆子说的这些沟里人沟里事谁都知道,可她要三番五次咻咻不止地说,谁也没阻挡过。
清明节过后第三天大清早,瑞娃拄根棍子沿沟顺河下来,到每家老邻居跟前说:“我今来有个喜事告诉你,我明天过生日哩,你门上锁都要来,我有儿女亲戚给拿的好酒好烟,平时攒的黄花木耳,拳芽香菇,还有核桃栗子,乃都是给儿女留的,他们不回来咱们吃!”

最后,她弯着腰、踉跄着到坡根治娃老汉门上,老土房门旁铁火盆里火烧的正旺,火上架个药罐子,冒泡呜嘟欢滚,烫气急冒飘散空中,治娃正在给瘫痪多年的老伴熬药。瑞娃老婆子颤颤巍巍抓住治娃树皮似的手说,“老哥!我知道你忙,经管我嫂子哩!我明天生日,我今给咱沟里二十三个人齐齐说,你能走离了也来。”说着仰脸很期待地看着。
治娃老汉腰成笼襻,灰白胡须布满颓丧脸容,双眼窝流露出漠漠无神的眼光,从瑞娃手中抽回自己粗糙厚皮老手,麻木地笑笑,双手为难似的搓捏着:“我、我忙,再、再说也没钱行情……”说话间头低得下下的,“国家给的低保养老金都吃了药了、都吃了药了……”
瑞娃老婆子心头一震,身子摇晃了一下,急说:“好哥哩!我咋能是叫你行情呢!我咋忘了给邻居们说呢!邻里还以为是叫行情哩!”手里的拄棍在地上杵了几下下,悔悟地叨叨说,“我老糊涂了没说清没说清,我咋忘了呢!我赶紧给重说去,我走了、我走了……”
她说完,弓腰趔趄着去了。
老婆子跌跌撞撞地又到各家各户再说一遍,重复又重复:“你来可千万别拿人情份儿,我乃山顶半坳两年多娃没回来,没人去冷冷清清,叫邻居去热闹热闹,我明天生日一过就七十六岁了,高兴高兴,绝杀我也没有想收人情礼的心思,千万不敢拿礼钱噢!”
叮咛再三、再三叮咛,到最后一家说完,眼里流出几滴泪水来,说得同岁邻居也伤心起来,陪着也眼泪汪汪。
第二天早上,沟里老人们起来早早的,刮胡子洗脸、换上干净衣服,沟下的邻居沿河道向上沟走时,经过山根河边庄子有人的邻家,高声大嗓喊叫着,“走——吃瑞娃老婆子生日走——治娃——”治娃站在埝塄大树底下高声应道:“来咧!来咧!”
不多时,串叫了四、五家,十来个老人个个圈拉着腰、拐拉着腿、说说笑笑地向沟上瑞娃老婆子家赶去。
瑞娃老两口在流岭大山半坳住着,还是早年盖的三间土瓦房,西墙边苫着小小一间炊房,庄子周围遍山参天大树,遮天蔽日,从远处看不到人家,山沟河里鸡肠似的小道,七弯八绕,盘来转去,通到半山坳瑞娃门上,小道两旁青蒿野草长得比人都高,各种小野花竞争开放,老头老婆子行走在蜿蜒的小道上,时隐时现。
沟下的老人们到瑞娃老婆子门口时十点多了,十多里的山沟小道崎岖不平走了一早上,难怪沟下人问瑞娃每天下沟底啥时动身,得到的回答是“天明能看见就走”。分布在左山右岭同组的四个孤寡老邻居天一明就来给瑞娃帮忙,洗菜做饭,沟下邻居家人十点多到门上时,早上饭已经做好,说笑打招呼后,饭菜端了上来,红豆稀饭、三笼香椿豆腐包子、醋溜洋芋丝、红油辣子蒜水水,老人们吃得香饱实在。
今个沟里上来了十六个老人,加上沟顶半山上的五个共二十一个,其余没有来的都是瘫痪在床,或者是脚腿不灵走不动的。
吃过早饭后,去的老人自己动手,缓慢笨拙地在场院墙边上支起做米饭二尺大铁锅,又一溜支起三个混菜铁锅,说说笑笑、欢喜热闹。瑞娃老俩囗换上了女儿给买的新衣服,脸上紧凑的褶子纹舒展开了,比平日精神多了,也没拄拐棍,屋里屋外说叨着,木耳在那香菇在这……然后拉住比她小五岁的女邻居手说:“妹子,这么大个庄子就我和老汉,冷冷清清。我门上许多年都没这么多的人,儿女两年没回来,一天刚打电话,这儿没电话信号,打电话要到沟下去哩!这若大的腰山组原先八十多口人,现在迁移的就剩我们五个老人了,野猪为王了。”说着牵手移到庄子高塄上,指着塄下长势很好、却东倒西歪的玉米说,“我和老汉坐到地里磨的做庄稼,都叫野猪糟蹋完了,收不到几背笼,多亏有政府给的底保养老金,不然没法活。”

瑞娃老婆子喊叫正在刮芋头的半老邻居:“家娃!你来给嫂子帮个忙!”
家娃停下手头活,随着进了屋,瑞娃指指炕头上一只大红桐木箱子说:“你劲大,把这给搬到房外院子里。”
家娃拘了一口气,搬起箱子撂到房外院子小方桌上。
瑞娃走到箱子前,撩起衣襟掏出一把小钥匙,打开箱子上的小锁子,堨开箱盖里面东西全晾了出来。来的邻居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,伸脖观看,有帽子、衣服、鞋袜,穿的戴的应有尽有,叠得整整齐齐,板板页页放着。
瑞娃取出一件抖落开,给围观邻居说:“这是儿子五年前回来买的!”又取一件抖落开,“这是女儿从外地买的,没穿过,净净新……”
把那一箱子衣物抖落完说完,忧喜交集:“我今七十六岁了,我能穿完这些不?我能穿烂这些不?养儿防老,咱这地方是狼不来,蝇子不下蛋,有儿说不下媳妇,早年跑出去入赘上门养活别人去了,早兴几十年移民搬迁多好呀!儿子不会成为别人家的人,最起码我和他爹的生日有人给过,不用咱们自己忙活——也不用亲人们自己上门做吃做喝。”
说毕已然失声,抱住比她小五岁的妹子悽情地说:“我想儿子呀?我有儿和没有儿一模一样,有女和没有女一样,我每夜每夜想的睡不着,盼天明。天明我不看这箱子,我叫他爹把这箱子搬的撂到板楼上,两天后可更想看,又叫搬下来……"
呜呜咽咽倾诉着,指指土房山墙边上一片地里柏树簇拥的一坐坟,又移手指指堂屋摞的两幅棺材,哽咽说:“这墓是我自己箍的,树是自己栽的,屋里棺材方子自己做,唯独没买老衣,老衣不用买,这一大箱子都是,春夏秋冬都有,我哪天和老汉死了,邻家百舍来给我或老汉把这穿上,一是省钱,二是娃给的,穿上娃买的衣服和娃在一起一样,睡到地里也觉得娃在身边……”
瑞娃说不下去了,悲伤欲绝、泣不成声,哭开了,来的女人也呜咽着,有几个老年人在一旁悄悄抹眼泪。
来的老婆婆用袄袖子围围眼泪,抽抽搭搭劝说:“老姐今个是你大喜日子,住到这荒山野坳,活到七十六都不容易哩,今个过生日高兴才对,甭想伤心事,甭说伤心话,甭要流眼泪……”
瑞娃忍了又忍,用袄襟擦擦眼泪,眼睛红红地抽泣:“不哭了,今日邻居亲人能来真真高兴,一辈子没过过生日,今自己过,热热闹闹、高兴、高兴……”
中午三点多老人们自己做的饭菜好了。土豆炖鸡块,木耳炒大肉,拳芽炒肉片,油炸豆腐,豆芽凉菜,黄花鸡蛋汤端上桌子。老人们欣喜欢畅、兴致勃勃。
瑞娃对老汉说:“把娃几年给拿的酒都拿出来,来的人都暍,我今儿最高兴,我也喝两盅。”
老汉进屋揭开大板柜盖,翻腾一会儿抱出来了四、五瓶酒,有西凤、太白、全兴、董公,往桌子一放,擦擦擦撕烂盒子说:“咱这儿偏僻没多的酒盅,今拿碗喝喝。”说罢取过大碗,每只碗里倒上酒,高声说,“我们自己祝贺自己,永远不老身体健康活过一百岁!喝!”
不分男女举碗同饮而尽。

太阳移到房子背后,饭吃毕了,老人们洗的洗碗、抹桌的抹桌,全院子拾掇得和原来一样,老人们准备回家了,瘦弱的治娃老汉从兜兜掏出皱皱巴巴一张百元票,窘红着脸恓恓惶惶、窣窣着递给送客的瑞娃老婆子。
“嫂子……我没多余的就这些,你拿着……” 治娃老汉说着,手抖动的更历害了。
瑞娃送客喜悦的神情骤然大变,像是血液凝固似的,脸色由红变青,嘴唇哆嗦手也发颤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照着对面的治娃“咚咚”磕起头来,断断续续地说“兄弟!你来、你来、把嫂子杀了、杀了、杀了算啦,我、我没有万元、万元钱,几千块有、有、有哩!”又磕起头来,“你、你在磕碜我嘿……”
瑞娃老泪横流。
邻里们赶忙搀扶起来,面面相觑,眼圈湿湿的。
治娃老汉胸口起伏,一股激情在胸腔间冲撞颠倒,震动的心悸眼花泪溢眼圈,惶惶不知所措,嚅动几下嘴唇,猛一扭头急急向沟下走去。
众邻居回家了,三间土房庄院又恢复了和往日一样的清净,山风吹来树摇叶响,鸟儿山上飞沟里叫音无准点,没有了白天的人声笑声,也没狗汪鸡上架的扑啦声,寂寞与冷清又包裹着瑞娃老两口怅然若失的心。
天黑了一会儿,上炕睡的时候,瑞娃问老汉,“今酒还有没有?”
“有哩!多着呢!”
“给我倒一大杯去,捡最好酒倒。”
“哎——你从没喝过酒么?”
“我今生日哩,高兴你知道不!”
“好!好!我倒!我倒!我给你倒去!”
一时老汉端来了能盛一两酒的大杯子,递给坐在炕沿上的老伴,老伴双手接过,端在胸前,双眼直勾勾盯着,酒杯微微晃动着洒出几点,瑞娃猛然间送到口边仰头一饮而进,把杯子递给老汉又说,“受活的很,一觉睡到天明,夜里甭叫我,跟你一辈子今个最高兴。”
老婆子解衣睡了,一辈子老两口习惯各睡炕一头。
第二天一大早,没见瑞娃老婆子拄棍下沟串游,而是老汉慌慌张张跑到沟下给邻居家人们说:“老伴过世了,咋晚上睡觉再没醒来,天明一摸身上冰凉……”
【作者简介】王英富,一九六四年出生,现年五十二岁,人称老王,现定居陕西丹凤县城。酷爱文学、爱读书闲时练写作。老王是个地地道道草根作者,自学写作,写的作品里都是左邻右舍,邻居同行间的趣闻轶事,语言质朴、幽默风趣、活泼耐看,乡土风味浓厚,百姓大白话,受到老百姓的喜爱热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【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《作家洪与》微信号:hongyupt
投稿邮箱:[emailprotected]
合作平台《琴泉》微信号stzx123456789
投稿邮箱:[emailprotected]
顾问:朱鹰 邹开岐
编辑:洪与 姚小红 杨玲
The End
-

- 洛北春38度(洛北春38度浓香型商务酒价格表)
-
2026-01-31 18:23:32
-

- blue labe价格
-
2026-01-31 18:21:18
-
- 贵州清镇黄氏酒厂(贵州清镇黄氏酒厂简介)
-
2026-01-31 18:19:03
-

- 夫妻吵架时老公经常提离婚(男人和妻子一吵架就提离婚)
-
2026-01-31 18:16:49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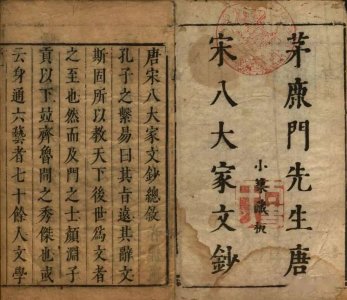
- 三苏分别是谁?你知道吗?
-
2026-01-31 18:14:35
-

- 新加坡 茅台(新加坡茅台价格)
-
2026-01-31 18:12:21
-

- 辞职报告书怎么写模板(员工辞职报告简短模板)
-
2026-01-31 18:10:06
-

- 端午节日记(端午节快乐日记(上))
-
2026-01-31 18:07:52
-

- 波特率是什么(波特率是什么意思115200)
-
2026-01-31 18:05:38
-

- 中国和印度战争是哪一年开始的(中国和印度战争是哪一年开始的唐朝)
-
2026-01-31 11:57:44
-

- 小米粥放糖还是放盐,小米粥放糖还是放盐养胃
-
2026-01-31 06:42:44
-

- 母亲节的祝福语,母亲节祝语
-
2026-01-31 06:40:30
-

- 挽回女朋友的信息,发什么消息可以挽回对方
-
2026-01-31 06:38:16
-

- 9年梧桐西凤酒价格表(西凤酒梧桐系列)
-
2026-01-31 06:36:01
-

- reno4se参数(分享1款oppo手机的参数配置)
-
2026-01-31 06:33:47
-

- 麦麸在饭圈是什么意思(麦麸怎么读)
-
2026-01-31 06:31:33
-

- 带泥莲藕的长期储存方法
-
2026-01-29 18:58:44
-

- 大风大雨将至!广州11区发布雷雨大风橙警,启动气象灾害Ⅲ级应急响应
-
2026-01-29 18:56:30
-

- 关晓彤综艺感?
-
2026-01-29 18:54:15
-

- 蛋挞常温放一晚上会坏吗
-
2026-01-29 18:52:01



 开封犹太人在中国17个姓氏,实际上只有七姓八家,现存6姓
开封犹太人在中国17个姓氏,实际上只有七姓八家,现存6姓 我国南方和北方是怎么划分的,你知道吗?
我国南方和北方是怎么划分的,你知道吗?